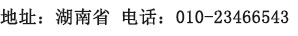毋庸置疑,在陕北说书的历史上,张俊功和韩起祥都属于“改革派”人物,但二人所走的路径却截然不同。如果说韩起祥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自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,以编新书、说新话,来迎合随时变化的政治形势,张俊功则完全相反,即使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,他也没有自觉向体制靠拢,以求分得杯羹,而是自觉回归民间,靠一把三弦、一副铜口钢牙将陕北说书由庙堂拉回炕头。
他的口头禅是,“我不爱跟公家人打交道”。他常对徒弟们说:“老牛力尽刀尖死,伺候君王不到头”,既然你不愿“伺候君王”,“君王”还会跑到安家坪问你:老张,有什么需要我帮忙?
回归民间,对张俊功来说就是把陕北说书在“文革”中以及更早年月里被掩埋、被破坏的东西打捞出来,重新上釉抛光,并让它再度回到乡间庙宇、农家小院等固有的舞台上。这个舞台被尘封得太久,以致于它一旦被清扫出来,便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。
陕北说书就主题而言,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古典戏曲、讲唱文学没有多大区别,不外乎“忠臣良将、才子佳人”的老般数。说书人也常常这样自曝家底:
闲官员编下书两本,
代代相传到如今。
一本叫奸臣害忠良,
一本叫相公找姑娘。
说书人离开这两本本,
再能行的行家也说不成。
“文革”复出后的张俊功并没有沿着韩起祥开辟的编新书、说新话的路子走下去,而是毅然扛起传统的大纛,回到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”的老路上。除了偶尔应景编个小段,如《一个存折》《老牛卸套》等,他从来没有把精力放到编新书上。
平时在乡间演出基本都是传统书,音像出版社为他录制的如《沉冤记》《清官断》《五女兴唐传》《武二郎打会》等都是传统书,只有一两个半新不旧的小段如《算卦》《懒大嫂》等。因而就说唱的内容而言,张俊功并没有多少创新。人们觉得它新,是因为这些旧的东西离开听众的耳朵太久了。
张俊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说书的音乐和表演的形式方面。
在说书音乐方面,张俊功博采众长,充分利用单音弦的技术特点,在原虎皮调的基础上糅合了眉户(劳子调)、梅花调、靠山老调、道情和秦腔音乐,去粗取精,成功地打造出了一种他称之为“迷花调”的音乐。这种音乐的最大特点是欢快、明亮,非常适宜现代人的耳朵。
陕北说书起源于乞讨,伴奏音乐历来以悲苦见长。原因简单:你上门要吃的,不把自己说得可怜兮兮,反而理直气壮或慷慨激昂,让施主听了觉得你比我还牛,还跟我要?我跟你走算了。后来又和神卜联结到一起,伴奏又显得阴沉、郁闷,尤其是韩起祥惯用的“靠山老调”和“巫神”很像。
张俊功和韩起祥虽同是横山人,但他俩同里不同派、同艺不同师,韩为三弦双音派,张为三弦单音派。韩派说书正宗古板,表现人物以平调哭音见长;张俊功说书活泼欢快,表现人物以平调花音见长,故有“韩帅张怪”之说。
张俊功熟悉陕北说书各流派的唱腔曲调,又大胆吸收各种地方小调、眉户戏、碗碗腔、秦腔音乐,甚至口技中的精华,并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说书中。加上张俊功本人闯荡江湖多年,善于模仿社会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语,这使得他的说书现场感强,气氛热烈。如悲伤时用虎皮调中的哭腔,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,但有时又会加进眉户戏中的“哭板”,使得唱腔细腻、婉转,一唱三叹。
武将交战用的是双音调中的武调,这种调式经韩起祥改编后紧张激烈、威武气派,战斗一起,就仿佛听见了千军万马的撕杀之声。但他的说书音乐最迷人的地方还在于“迷花调”的反复响起。经他改编后的“迷花调”柔美、动听,一扫传统说书的质木无文和阴沉悲苦之气,使得听书成为一种享受,而不再是为“哄神神”而受罪的差事。
在表演形式方面,张俊功最大的贡献是,大但借鉴了戏剧表演的形式,将陕北说书由“坐唱”改为“站唱”。
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。陕北说书自诞生以来,就是坐着唱的,“坐唱”的历史和陕北说书的历史一样长;但现在这个半盲人将它改为“站唱”,好比爬行的猿人突然开始直立行走,令好多艺人目瞪口呆。
这不是改良,而是革命。这场革命据当时的参加者、张俊功的儿子张和平回忆,发生在年的2月:
那年我已经虚岁16了,会弹三弦了。常和我爸(张俊功)串乡演出。有一天前晌,记得刚过罢正月十五,我们俩到我们村对面的潘圪坨说书。我爸一直就会打四片瓦,常在演出开始之前说快板,不算“正场书”,只能说是“打耍耍”。那天说完快板,要开始说正书了,他突发奇想,说:“我看人家唱戏的,是站下唱了。咱们也试试,你坐下弹,我给咱站起来说,看怎么样?”说完,他就打起四块瓦说开了。村里的几个老汉儿稀奇得不得了,说“活了一辈子了,从来没见过个站起说书的。这个好!又能听,又能看。”从那天开始,我们说书就再没有坐下过。以后带的徒弟多了,又加了二胡、板胡、笛子、马锣等乐器,但人再多,主说的人也一直是站着的。
从坐到站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转换,而是由弹唱分离带来的表达自由。这种表达自由是前所未有的,说书人的身体从此由怀抱三弦的坐姿中解放出来,可以随意表演动作,并在舞台允许的范围内来回走动,这使得说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听觉艺术的局限,有了初步的视觉艺术的效果。
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自由,有的人天生就恐惧自由,就像华阴老腔,原来只是附属于皮影的幕后戏,后来才撤掉幕布,与皮影分家,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。刚开始撤掉幕布后,好多人无法适应。原来有一块幕布挡着,好坏美丑都看不见,现在一切都曝光在众人眼皮底下,许多唱家都张不开口了。他们说,来的都是乡党,臊得很!说书人也一样,他们坐着说唱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了,现在突然让他站起来,他不知道干什么。
尤其是对那些双眼失明的艺人来说,这场革命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因为身体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站起来表演。张俊功之所以能创新成功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他的右眼能看见。加上他从小会唱戏,爱丢丑,这些因素加起来才使他的革命能够成功,而对于大多数盲艺人来说,走路都要人扶,遑论站起做动作?加上本身缺乏表演天分,生计就越来越困难了。
因此,就像当年韩起祥禁止说书人卜命算卦一样,很多盲艺人有意见,说:你进了公家的门了,有饭吃;我们是受苦人,没吃处。你说算命不顶事,顶事不顶事那是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碗饭嘛!现在张俊功将“坐唱”改为“站唱”,说书人群起而仿效,盲艺人本来就光景不好,现在站不起来,更没人要了。
因而,很多盲人对张俊功恨得牙痒痒,认为就是这个“坏怂”砸了他们的饭碗。直到年,当张俊功去世的消息传到延川后,盲艺人白旭章竟然幸灾乐祸地说:“咋把一个害除了!”
但对那些有表演天分的明眼人来说,张俊功的革新无异于锦上添花。陕北话说“正想上天了,等上个龙抓”,有些人在张俊功将陕北说书革新后如鱼得水,如虎添翼。如子长县有个说书人叫贺四,从小就跟着父亲唱道情,他演的丑角戏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,在当地很有名。16岁拜当地一个老艺人为师,学习说书,但一直进展不大。25岁时改投张俊功门下,技艺大长。
虽然由于年轻时过度用嗓,不懂得保护,把嗓子说坏了,但他把演丑角戏的“童子功”用到了说书上,使他的说书生动活泼,喜感十足,很受观众追捧。在这些有表演能力的人成功转型后,那些表演稍次的艺人,在市场刺激下也不得不改弦更张,寻求突破。
短短十来年功夫,艺人们从口才、形象、到动作、台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经过近五十年的舞台实践,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,“站唱说书”拓展了陕北说书的表演空间,释放了演员对剧情的想象力,从整体上提升了陕北说书的舞台魅力。
(未完待续……)
往期回顾:
①狄马: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——以韩起祥、张俊功、王学诗为例(一)
②狄马: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——以韩起祥、张俊功、王学诗为例(二)
③狄马: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——以韩起祥、张俊功、王学诗为例(三)
④狄马: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——以韩起祥、张俊功、王学诗为例(四)
未完待续,敬请期待手机用户打赏渠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